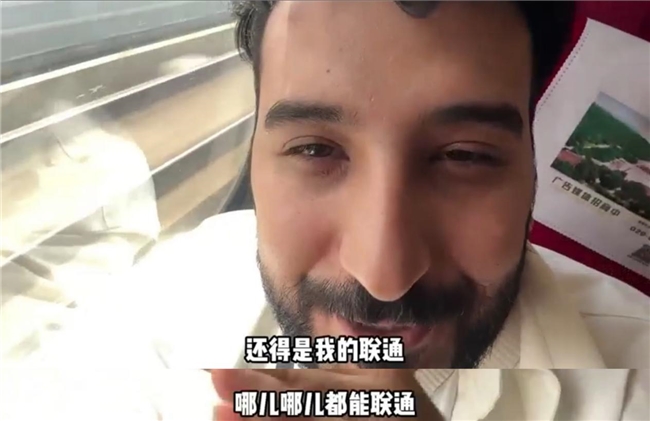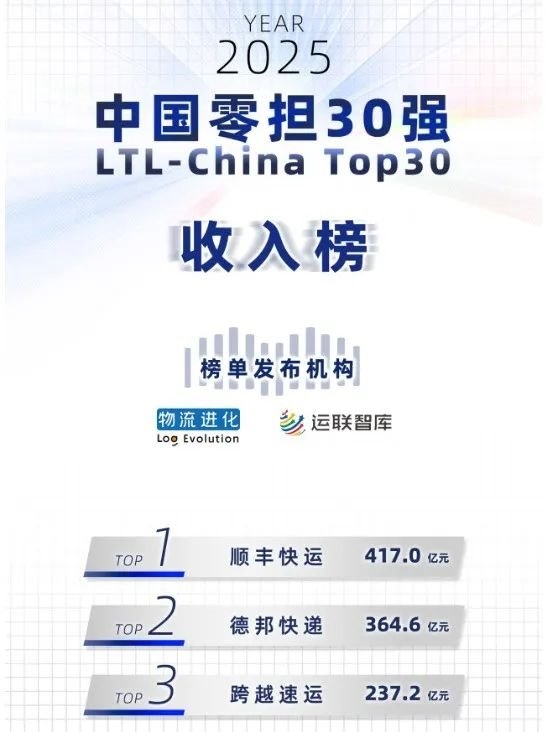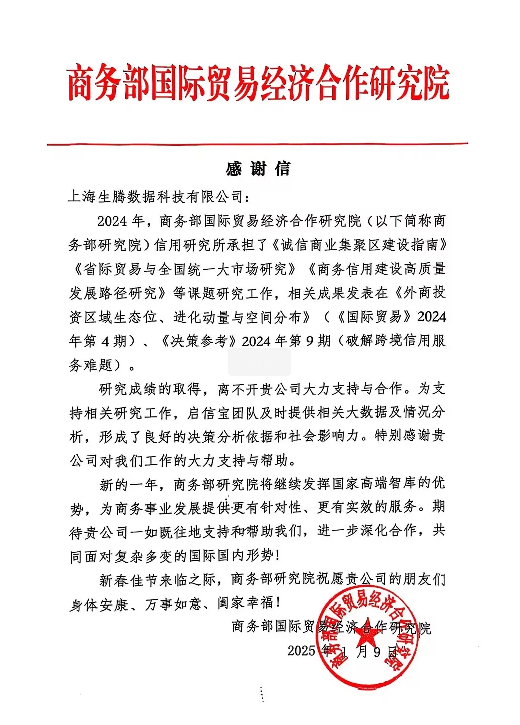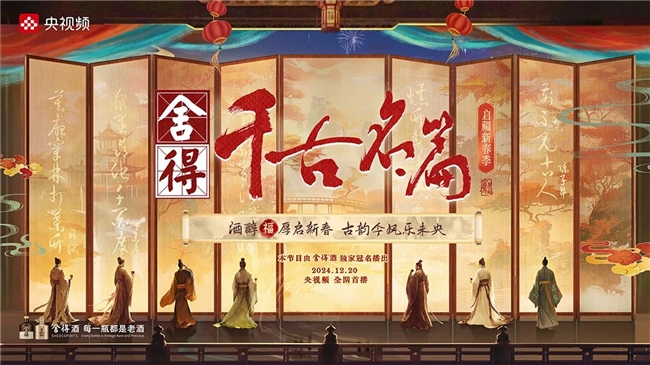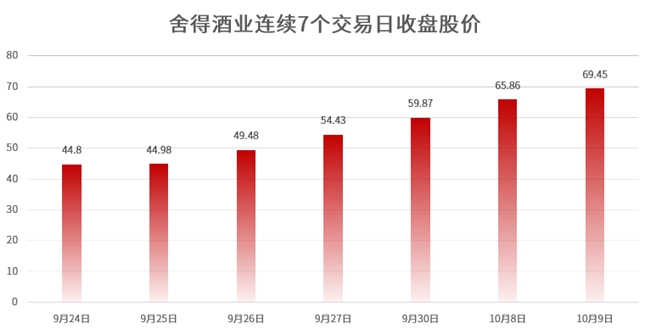(资料图)
(资料图)
早上买菜时,菜市场出口处的香樟树下,蹲着一个附近农村的老人,面前摆着一个篮子,篮子一边覆盖着一条毛巾,毛巾下黄澄澄的,我眼神不好,弯腰问她卖的什么,她说是横子。哦,原来是杏子黄了。
在小城的土著口中,杏子是叫“横子”的,“横”读汉语拼音第四声,强横的“横”音。刚来小城时,觉得这个发音很土,一想到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要读成“横花”,简直无法忍受,便越发对“横子”发音非常抵触。
后来,我去江南名城芜湖、南京、扬州和苏州等地出差,竟在寻常巷陌也听到“横子”的念法,当真非常惊讶。这么旖旎的江南,如此深厚的底蕴,何至于也有这样不雅的念法?在南京仓巷,我问一个正在吃“横子”的老先生,他看了我一眼,短哼一声说:“我小时候,我爷爷就是这么念的,怎么就不对了呢?”
我问他,在念宋词唐诗时,是不是也这样念,他说是的,他念了一句“杏花疏影里,吹笛到天明。”深情悠远,声音低回。我听呆了,原来这般念法,别有一番古韵,那是普通话无法企及的古色古香。
回去翻《康熙字典》,里面明明白白地写着,“杏”有两种读音,何梗切念“横”、下梗切念“杏”。值得玩味的是,编于唐开元年间的《唐韵》,以及编在明开国洪武八年的《正韵》,讲明杏音“横”,而夹在两者之间的宋代、元代,却是杏子的现代读音。
后来,我有幸现场听叶嘉莹先生用唐音来“唱”古诗,颇为震惊。诗歌除了要表达的意境和意味,那种风神和韵味,也只有用那时候的形式来表现。吟诵当然要用当时的音韵,叶先生说如此才能揣摩古人的精神。读音绝非只是换一种方式念念那么简单,它藏着记忆和文化,譬如我自己,读“小溪”时的感受,就远不如念“涧滩”,后者,才能令童年、村庄的记忆一下子变活泛。
我所生活的这座小城正是江南,吴头楚尾,是杏花春雨江南的背景。草木年年枯荣,这片大地上的人,也像潮水一般涨落。千年过去了,杏花开了千回也落了千回,在寻常巷陌,在山野之间,犹有人用古音呼唤它的乳名,那斩不断的文化血脉,依然还在。
作者:古水草
来源:扬子晚报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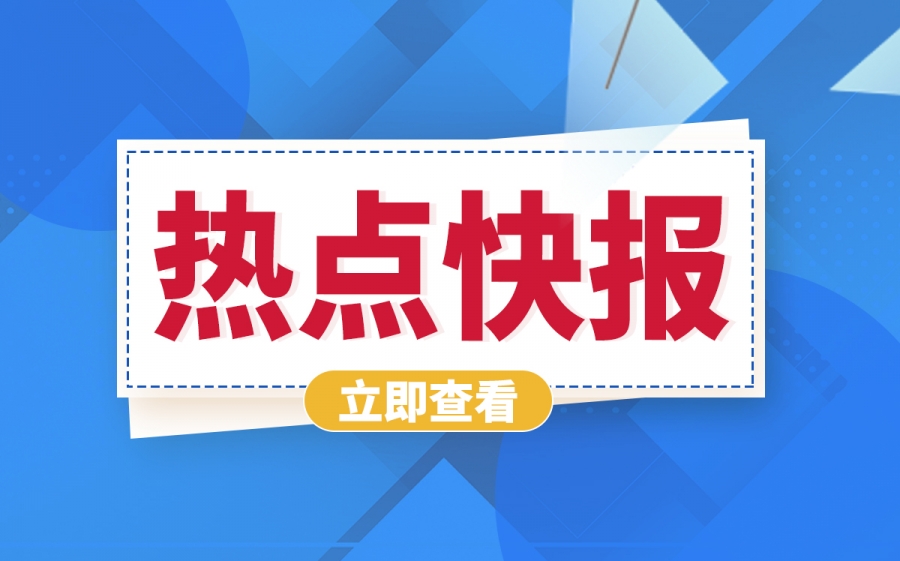



![星之海至日神殿岛解谜攻略 至日神殿岛图文解密图文一览[多图]](http://www.jxyuging.com/uploadfile/2022/0610/20220610012244670.jpg)